您现在的位置:
2015-12-23胡经之:我发现,在深圳做学问,还是要向“新、精、尖”方向发展
来源:深圳晚报发布时间:2015-12-23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在1984年过“知天命”之时,竟会从国内最古老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来到当时最年轻的初创大学深圳大学,所为何来?
那是因为受到了深圳的盛情相邀,为新时代的召唤而鼓舞,来到这方正待开发的处女地作我一生中的最后一搏。
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我参加不了硬实力建设的行列,只能为经济特区的初创在软实力建设方面出一些菲薄之力:一是较早开展了国际文化交流,二是开始了人文学科建设,三是参加了特区文化研究,推进了文艺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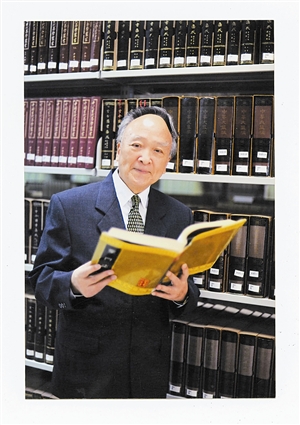
壹
我在这里亲身体验到了正在发生伟大变革的时代气氛,受到了强烈感染。……我俩一致决定,立即向张维校长回复:跟他去深圳
应时代精神召唤
正当我在北大全神倾注于学科建设之时,1984年元旦,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院士约了我和汤一介在清华园寓所见面。张维院士是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常出入于国际名校,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向了如指掌。时任深圳市市长梁湘下决心要创办一所新型大学,就请了他来担任首任校长,从头开始设计深圳大学的发展蓝图。
张维院士一见我俩,就开门见山,直言相告:深大志在发展新兴学科,但一定要办中文系,而且一定要办好,不然,怎么成得了综合大学。他已向国家求援,和北大打了招呼,要北大支援深大的人文学科建设。他告诉我俩,他已请了北大副教务长、英语系主任李赋宁到深大任外语系主任;现在想请汤一介来当国学研究所所长,乐黛云和我当中文系主任,半年在深大,半年在北大,依托北大的实力,迅速为深大开拓人文学科。
当时,我和汤一介都对深圳所知甚少,心中没数,不敢贸然答应,愿回去考虑,再作回复。
就在此月下旬,邓小平亲到深圳考察,对经济特区的建立作了充分肯定,我亦心有所动。百闻不如一见,汤一介要我亲身去那里体验一下。我在那年“五四”真的去深圳考察了一番,深切感受到这里意气风发的时代精神,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所吸引。从清华大学来担任深大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的罗征启,办公室主任、江苏老乡王克来,北京文友、特区报副总编许兆焕,以及几位早就应聘来此的北大学子张卫东、刘丽川、钱学烈等,都劝我早些来,共同投入深圳的文化教育建设。甚至,几位来深圳作考察的美学同行蒋孔阳、李泽厚、刘纲纪等,也都看好这里国际文化交流的前景,齐声称好。
尽管我只是在这里转了一圈,但就如我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到北大时见到的海淀镇一样,说不上有多少好感。我在这里亲身体验到了正在发生伟大变革的时代气氛,受到了强烈感染。我一回北京,立即把我的观感告诉了汤一介。我俩一致决定,立即向张维校长回复:跟他去深圳。同时,汤一介又迅速敦促远渡重洋、在美国访学的乐黛云,及早回国,一起去深圳。
1984年9月,由张维校长亲自率领,带了北大的李赋宁、汤一介、乐黛云和我4人,清华的图书馆馆长唐统一、建筑系主任汪坦、电子系主任童诗白3人,以及人大法律系主任高名煊,乘飞机到广州,再奔深圳就任。在新校落成和开学典礼上,张维校长把我们这些人介绍给当时的市长梁湘和副市长邹尔康相识,并迎来了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罗亢烈,澳门学者程祥徽,开启了对外文化交流。从此,我和深圳结下了不解之缘。

贰
当我把深大邀请我们去的消息告诉季羡林和杨周翰时,他俩都大加赞赏,热忱鼓励我们去深圳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文化交流平台
启国际文化交流
回想当初,深圳最先吸引我的,是这里得天独厚、便于构筑国际文化交流的理想平台。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决心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向世界开放。多年担任北大副校长的季羡林积极响应,早在1980年就和杨周翰、李赋宁发起在北大迅速建立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的有效机制,并于1981年1月在北大正式成立了国内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会。但在当时的北京,国际文化若要进一步推进交流,还是困难重重,手续繁多,中国学者要出国,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当我把深大邀请我们去的消息告诉季羡林和杨周翰时,他俩都大加赞赏,热忱鼓励我们去深圳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文化交流平台,一南一北,遥相呼应,通力合作,推进国际文化学术的进一步交流。
北大的这一期待,不仅符合了我们的学科发展需要,也切合了经济特区的发展方向。经济特区创办的目的,是要向国际化城市的方向迈进,开拓国际文化交流,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一到深大,在创立国学研究所的同时,立即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所,这属国内首创。1985年,在邓小平手书“海上世界”的明华轮上,举办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年会,近百位国内外著名学者云集深圳,这是深圳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创举。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佛克马以及美、法、日等国的比较文学学会主席,都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季羡林和杨周翰也亲来出席此次盛会,分别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和主席。
国学研究所也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1985年,汤一介在此主持了“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交流,海外学者杜维明、魏斐德,上海学者王元化、朱维铮,北京学者庞朴,武汉学者冯天瑜,广州学者张磊、袁伟时等都来到深圳,引起了文化学界的关注。
规模更大、影响更广的一次盛会,乃是在1986年召开的“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国内外竟来了100多位学者和作家,盛况空前,且首次迎来了不少东南亚的华文作家,更远的美国、澳大利亚也都来了人。这次盛会,甚至吸引了市政府的关注,当时即将调任海南省当省长的梁湘和副市长邹尔康,都兴致勃勃地赶来深大粤海门,坐在听众席上恭听海外友人讲说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发展现状。
之所以能在经济特区草创之初就如此顺利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倒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能耐,而是因为较早地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得风气之先,适度超前,先行先试。当时,北京的国际文化交流渠道尚不畅通,深圳却得天独厚。海外人士只要持有到香港的护照,就可直接从香港入深圳“旅游”,不必再到北京办签证。当初市政府忙于八大文化设施的硬件建设,尚未来得及抓软件建设。而我们从学科建设的需要出发,在深大先走了半步。从此一发不可收,不时举办国际美学研讨会、西方文艺理论研讨会等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因为恰逢其时,因而显得一枝独秀,引人瞩目。

叁
我和副手章必功、景海峰、张卫东等商定,把学科方向扩大,把文学比较扩展为文化比较,中文系扩建为国际文化系,办学方针为:沟通中西,应用为主
推人文学科建设
来到深圳的第3年,我又面临着一次人生选择。1984年我到深圳时,王学珍正提升为北大党委书记,张学书不仅是副书记,而且又兼任了第一副校长。张学书虽同意我到深大支援发展新兴学科,但一再叮嘱我只去3年,重心还要在北大,然后回来。到1987年,他一看见我,就敦促我快回北大,别再去深圳了。
那年元旦,我到清华园向张维院士拜年,从而有了一次长谈。他知道我一直不适应北京的气候,而到深圳之后,很快适应,精神振奋。这位慈祥长者衷心劝我,留在深大罢,继续为发展人文学科多作贡献。
也就在这一年,北大中文系主任严家炎从美国讲学回来,很快就代表学校找我作了一次正式谈话,要我尽快回到北大,并为北大争取设立文艺学博士点。因为家炎乃我攻读副博士研究生的同窗好友,可以推心置腹,我就向他说了肺腑之言:我已喜欢上深圳,不回北大了,请他向王学珍、张学书致意感谢。家炎看我去意已决,也就不再阻拦,答应把即将毕业的研究生王岳川留下,继续在北大发展文艺美学这一专业方向。
从此,我就定居于深圳,不再飞来飞去了,从而可以安下心来,专心于人文学科建设。此时我开始设身处地为学生想:这样的学科设置适合经济特区发展的实际需要吗?
我和当时主管文化教育的副市长林祖基在银湖等地开会时多次畅谈深大的人文教育。林祖基对我坦诚说道:在深大要发扬北大的人文学术精神,这是大好事。但如何能发扬好,还是要多动点脑筋,考虑好如何和深圳的实际需要相结合。深圳要向外向型的国际化城市发展,急需中西通的通才,专业不要分得太细、太专。
我觉得他说得在理。经过反思,我和副手章必功、景海峰、张卫东等商定,把学科方向扩大,把文学比较扩展为文化比较,中文系扩建为国际文化系,办学方针为:沟通中西,应用为主。这在当时乃是深大首创。我又在国际文化系开辟了不少新的专业方向,如大众传播、对外汉语、旅游文化等。后来,吴予敏把大众传播专业发展为传播学院,郁龙余把对外汉语专业发展为国际交流学院,景海峰主持的文学院在中文系之外,又建立了历史系和哲学系,令人鼓舞。
过了“耳顺”之年,我本可以退休了,但199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了我为深大建校以来自行产生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不能就此退休,就由此而延长了11年,培养了10届文艺美学博士生,到71岁时才告退。我稍感欣慰的是,在我即将退休之前,还与暨南大学原副校长饶芃子合作申报,为华南争取设立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到了新世纪,中山大学也被增设为文艺学博士点,我有幸被邀,又在中山大学招收了文艺美学博士生,再次出了点菲薄之力。只是我有点愧对北大,有负家炎师兄当初的一番好意。

肆
我不仅有了“深圳情怀”,还从“读万卷书”走向了“行万里路”,不断出国考察,多了些“国际视野”。我逐渐发现,在深圳做学问,最适合做的还是要向“新、精、尖”方向发展
倡特区文艺评论
在深圳落户定居之后,市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宣惠良就来动员我去市里接替祝希娟担任文联主席。我更愿意在校园里教书做学问,并没有去任专职,但还是和祝希娟、王子武一道被推选为兼职的文联副主席,又当了10年的作家协会主席和名誉主席、评论家协会主席。
对我不愿去市里当文联主席,林祖基倒颇谅解,尊重我的个人意愿。但他劝导我,在深大做学问,也应关注经济特区文化的发展,要及早对特区文化进行研究,为特区培养文化建设的人才。我敬佩他有这样的超前意识,就在建立国际文化系的同时,成立了特区文化研究所,很快开办了特区文化研究班。这研究班先后开办了两届,约30人,当时的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副局长、文联秘书长等都来了。校长罗征启亲自向大家宣布,若经专家评审,成绩优秀者,均可发给研究生文凭,甚至授予深圳大学的硕士学位。林祖基对此也首肯,鼓励大胆改革。但后来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就难以推进了。
那时的深圳文艺界,创作和评论双翼齐飞,紧密配合,良性互动,相互促进,深圳特区报还设立了“文艺评论”专刊,在国内传播。我还尝试把文化研究和文艺评论结合,对特区文艺的发展道路作些理论探索。在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10周年之际,我和时任文联主席董小明共同主持了《深圳文艺理论批评丛书》多卷,我为丛书写了序文《文艺评论求创新》,突出了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的相互作用,共同要为实现真、善、美的终极目标而全力奋斗。
做文化美学研究
我蛰居北大校园30多年,一直水土不服,对北京的气候未能适应,时常过敏,不得安宁。初到深大的后海湾校园,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空气清新,周身舒畅。以后我走出国门,作了比较,惊异地发现,深圳的山海胜景,毫不比芭堤雅、夏威夷、新加坡等地逊色,只是藏在深闺人未识而已。于是,我的“深圳情怀”油然而生。
更使我感到亲切的是这里的人文关怀,平等待人,洋溢着人间温馨。逢上深圳进行工资改革,时任市委书记、市长梁湘发话,他不要拿最高工资,教授、专家的工资可以高于市长。落实下来,我和毕业于牛津大学的李天庆副校长都拿到了高于市长的最高工资,在深大校园成为美谈佳话。全市统一安排住房,也不是仅凭行政级别为准,而是把贡献、成就等一并考量在内,依综合得分的高低来分配,这样,我和晚来的牛憨笨院士却能在全市最先挑选住房,得以安居乐业,潜心做学问。
我不仅有了“深圳情怀”,还从“读万卷书”走向了“行万里路”,不断出国考察,多了些“国际视野”。我逐渐发现,在深圳做学问,最适合做的还是要向“新、精、尖”方向发展。
深圳为学者培育了可以做“新、精、尖”学问的土壤,较早就成立了杰出专家联谊会。那几年,每当召开专家联谊会,市委书记、市长就专程前来和大家座谈,亲自听取专家对深圳今后发展有何高见,上下交流,直接沟通,相互间以朋友相待。
黄丽满任市委书记后,在春节召开文艺座谈会,晚宴上一直耐心听我对深大发展发表的意见,并很快付诸实践。这不仅使我感到欣慰,而且受到鼓舞,使我更多地关注深圳的现实,思考如何在此构筑共同的精神家园,在文化学术界倡导“从文艺美学走向文化美学”,开拓更宽广的人文学术之路。
我从北大到深圳,远离了我国人文学术的中心,走向了边缘,但人文学术界没有疏远我,中国文艺理论学会选我当了副会长,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也推我为副会长,我至今还担任着《文艺理论研究》《文学理论前沿》《中国美学》等学术刊物的学术顾问。上世纪90年代,国务院为我颁发了“为高等教育作出了突出贡献”证书,2015年,我还被广东省评为“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成为深圳市首位获此荣誉的人文学者。但我清醒地意识到,这并不是因为我个人有多大的学术成就,给我个人荣誉的背后,承载着对经济特区的热切期待,希望在这改革开放前沿的热土上,应该而且能够产生出更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术精品。
感恩深圳之后,引发了点滴余想。深圳已经走过了三十而立之年,正在向现代化、创新型、国际化城市方向高歌猛进,在高度重视高新科技发展的同时,理应更加重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智库建设。这就不能只靠个人单打、孤军奋斗,而要组织有力的团队,社会科学,乃“为人之学”,需要密切关注社会公共问题,必须集思广益,通力协作,共同攻关,才能奏效。“深圳学派”要发展,恐要在分工协作上还要多下些工夫,以求形成整体合力。
胡经之
1933年出生于无锡。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文艺美学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及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的顾问、广东省美学会会长等。在北大攻读文艺学副博士课程时,师从杨晦学文艺学,又随朱光潜、宗白华习美学。著有《文艺美学》《文艺美学论》《胡经之文丛》等。
本期历史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口述时间
2015年12月9日上午
口述地点
上步中路1004号深圳市政协
本期整理:深圳晚报记者 施展萍 实习生 庄楠楠 杜婷 黄丽云
前期统筹: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编辑:蔡励敏